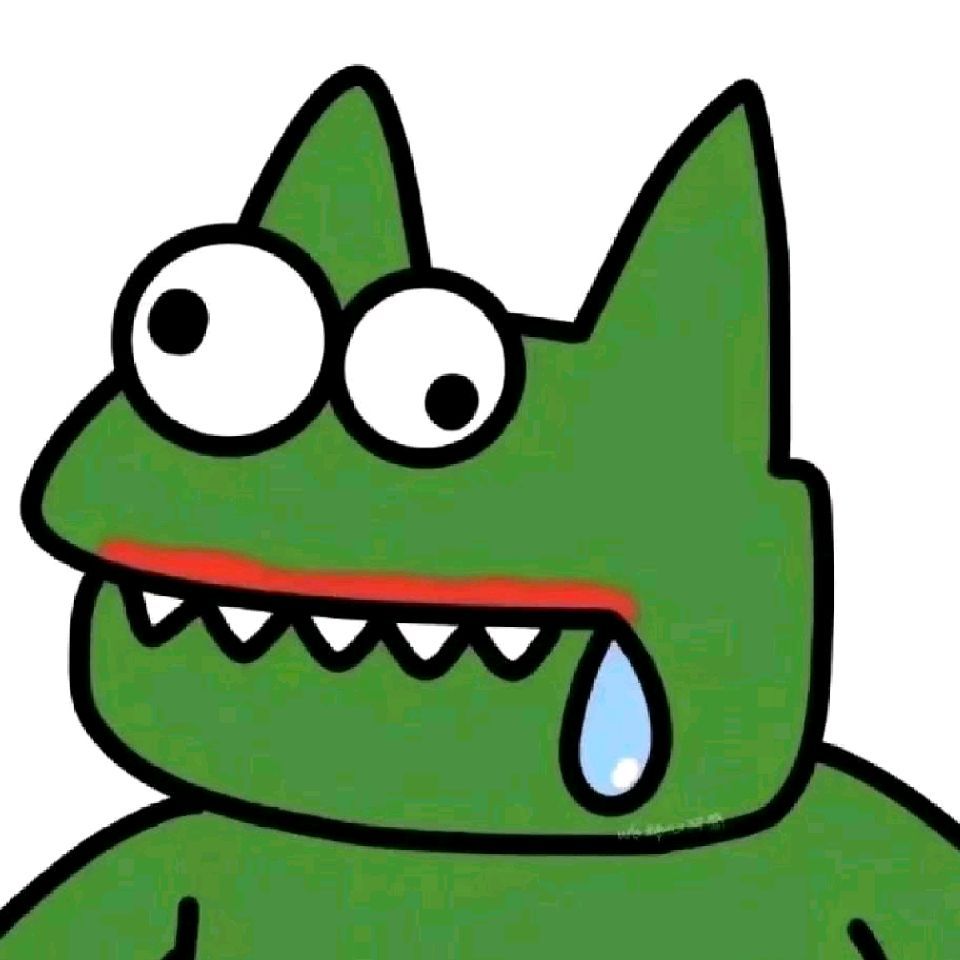
吧务
level 13
责任知识论的核心在于(Ultima facie epistemically responsible)认知上底定负责的 并且知识要认知上底定负责而成功(success because of being ultima facie responsible)
这里底定负责=认知负责 +不缺少相关信息
认知负责=需要认知过程的epistemically blameless(无可指责)且发挥认知能动性(epistemic agency)
epistemically blameless(无可指责)常见例子包括粗心大意,在重要问题上没有仔细观察或调查就下结论,坚持把抛硬币、主观愿望等不是证据的东西当作证据(无视他人提醒),对反面证据视而不见,等等。如果正常人犯了这些错误,我们就可以从认知角度指责/批评他们
2025年10月09日 02点10分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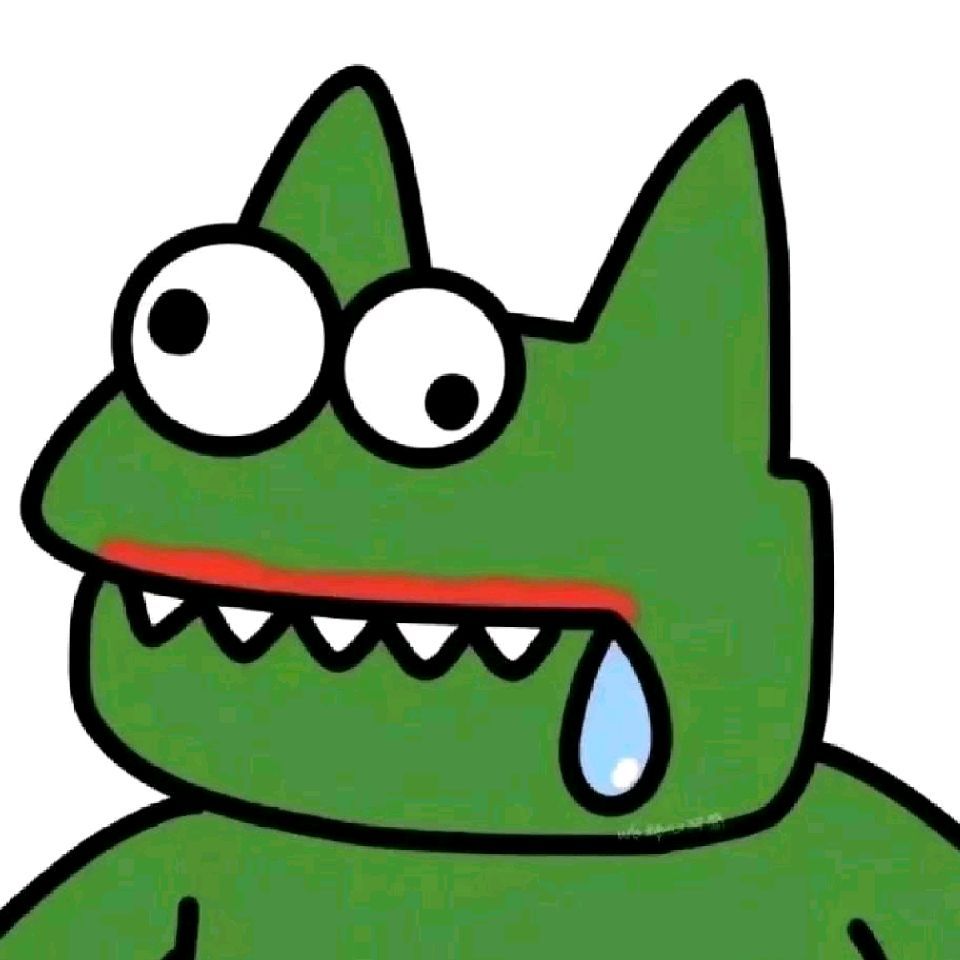
吧务
level 13
胡的定义是
(在t时刻)S 知道p,当且仅当(在t时刻)S 之所以相信真命题p,而没有相信某一个非p选项,是因为S的信念形成方式是认知上底定负责的。认知上底定负责=认知上负责+没有真正的削弱者。S是否以认知上负责的方式相信p,不仅仅依赖于相关的道德/福祉风险,也依赖于S的认知能力和社会角色。
2025年10月09日 02点10分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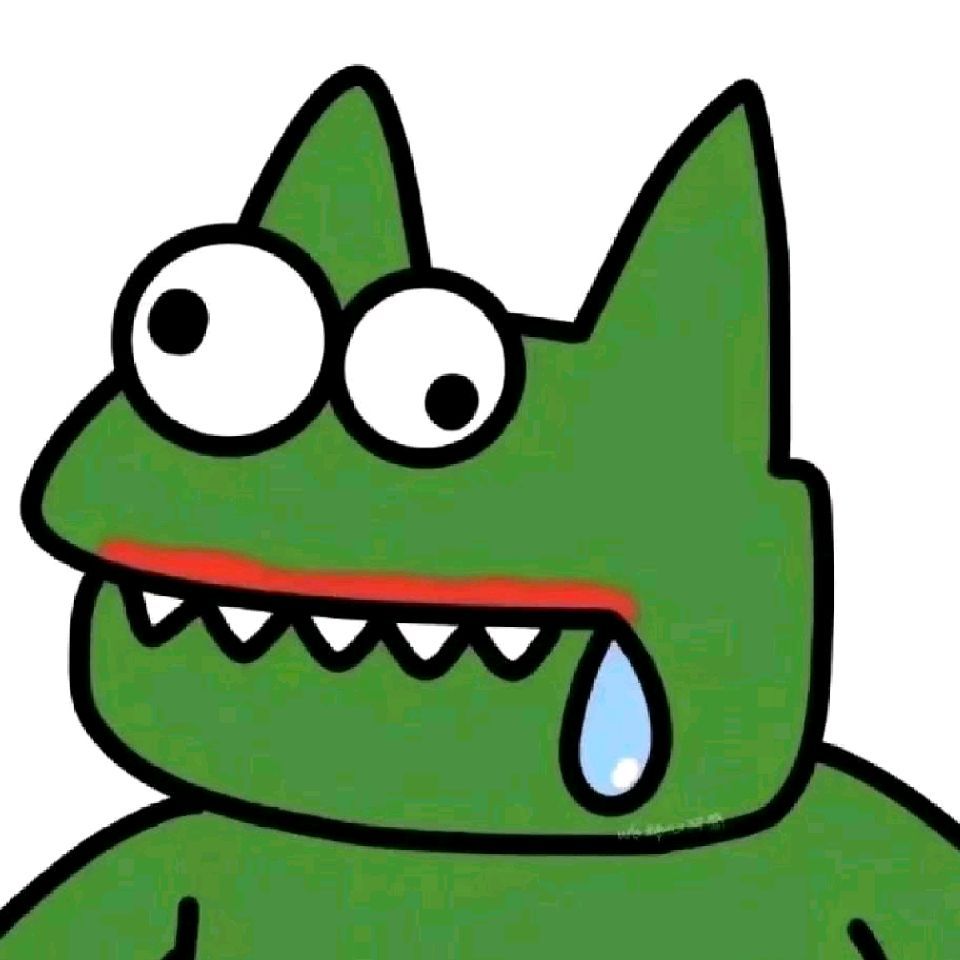
吧务
level 13
我的思考主要在书中的这段话针对责任知识论对 新怀疑主义
以下是原文
对于新怀疑主义问题,责任知识论可以给出类似的回应:假设我是一个商场的销售员,从未想到怀疑主义假设,此刻基于清楚明白的观察相信前方有一个人。即使我的证据平等地支持怀疑主义假设我也是以认知上负责的方式相信前方有一个人:我发挥了自己的认知能动性,并且在认知上无可指责/批评。从认知角度,我没有责任去考虑怀疑主义假设。要求一个不研究哲学的人去考虑怀疑主义假设,显然是很过分的认知要求。
此外,如果我事实上生活在认知桃花源中,我的信念形成方式不仅是认知上负责的真信念,而且是认知上底定负责的真信念,因为不存在削弱者。在认知桃花源中“我一直被恶魔欺骗,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象”只有逻辑或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完全没有现实可能性。如果我意识到“我一直被恶魔欺骗,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象”只有逻辑或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而没有现实可能性,并继续基于自己清楚明白的观察相信前方有一个人,依旧是认知上无可指责/批评的。一个类比:你基于记忆和观察,相信你此刻看到的人是你一个星期前约会过的人。后来你意识到“你此刻看到的人是恶魔幻化的,不是你一个星期前约会过的人”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但有逻辑或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而你继续基于记忆和观察相信你此刻看到的人是你一个星期前约会过的人,这不是认知上不负责。
有人会问:如果我事实上生活在认知桃花源中,但不是一个从未想到怀疑主义假设的商场销售员,而是一个研究知识论的哲学教授对怀疑主义假设熟悉,并且我的证据平等地支持怀疑主义假设和非怀疑主义假设,那么我还能以认知上负责的方式相信怀疑主义假设是错误的吗?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一个研究知识论的哲学教授似乎没有(认知上的)责任去搜集更多的证据去否定怀疑主义假设。他可以相信怀疑主义假设是错误的,同时合理地质疑“如果S的总体证据平等地支持p和某个非p选项,并且S意识到那个非p选项,那么S就不应该相信 p”这一认知规范。为什么这一认知规范是错误的?不同的哲学家可以给出不同的回答。我的回答是:如果S的总体证据平等地支持p和某个非p选项,并且意识到那个非p选项,但S没有(认知上的)责任去搜集更多的证据去否定那个非p选项,那么S可以基于原有的证据相信 p。 比如,我从星巴克出来,刚好碰到老王进人星巴克。三分钟后,我在路上遇见老孙。他说在找老王,我告诉他老王在星巴克。显然,我基于三分钟之前看见老王走进星巴克而相信老王此刻在星巴克,是认知上负责的。虽然我的证据同等地支持'老王还在星巴克”和“老王一分钟前已离开星巴克”两个命题,但我没有(认知上的)责任去搜集更多的证据去否定“老王一分钟前已离开星巴克”这一命题,即使我意识到老王可能一分钟前已离开星巴克。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比如关于怀疑论 好像知识论的哲学教授似乎有(认知上的)责任去搜集更多的证据去否定怀疑主义假设,因为如果这个问题不是知识论哲学工作者面对,其他人就更没有认知义务搜证怀疑论的内容了。
第二个问题:证据相同没有认知义务搜证当作证据充分可相信的理由选择相信p而不是 ¬p我觉得很诡异这个观点啊?换句话说,“不需要去查”并不等于“该相信”。
2025年10月09日 03点10分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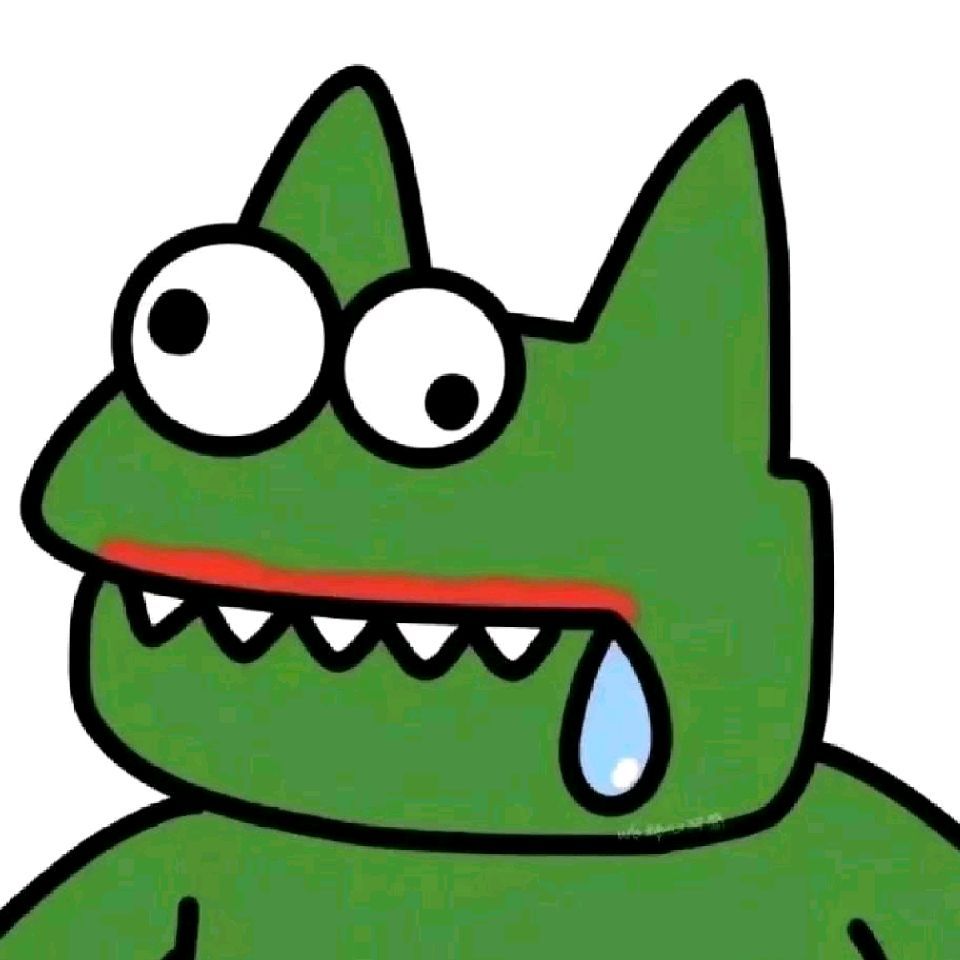
吧务
level 13
胡老师的回复
我在书中说,认知责任并非一个绝对、统一的标准。它与我们的社会角色、认知能力,以及至关重要的一点——问题的道德和实践风险——紧密相关。一位调查谋杀案的警探有极大的认知责任去搜集证据,因为道德风险极高。相比之下,回答一个琐碎问题所涉及的认知责任则要低得多。
怀疑论的哲学问题,虽然在智识上引人入胜,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通常不带有直接的道德或实践风险。相信我的手是存在的,即便我承认恶魔欺骗我的逻辑可能性,这个信念我也可以在认知责任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持有,因为犯错的实践风险微不足道。正如我提到的,“怀疑(或否定)我自己是正常人,对我的道德和福祉风险才非常高。因此,要怀疑(或否定)我自己是正常人,才需要收集非常强的证据并做深度思考”。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提供证据的责任在于怀疑论者。
教授的职业责任是研究、理解和讲授怀疑论问题——即分析论证、权衡现有证据、并探索潜在的解决方案。这不同于通过搜集决定性的新证据来解决此事的个人认知责任。那种能够一劳永逸地排除“恶魔假说”的证据,根据该问题自身的定义,似乎就是无法获得的。因此,教授并没有一条清晰的路径去像警探那样“搜集更多证据”。他们的责任是处理既有的论证。在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去接受怀疑主义假设(这会给我们的整个信念系统带来巨大的颠覆性成本)的情况下,教授继续持有非怀疑论的默认立场,在认知上是负责的,即使他同时在专业上分析这个僵局。
第二个问题直指“星巴克”例子的核心。那个例子是:我从星巴克出来,刚好碰到老王进入星巴克。三分钟后,我在路上遇见老孙。他说在找老王,我告诉他:老王在星巴克。显然,我基于三分钟之前看见老王走进星巴克而相信老王此刻在星巴克,是认知上负责的。虽然我的证据同等地支持“老王还在星巴克”和“老王一分钟前已离开星巴克”两个命题,但我没有(认知上的)责任去搜集更多的证据去否定“老王一分钟前已离开星巴克”这一命题,即使我意识到老王可能一分钟前已离开星巴克。
在我的理论框架内,这可能不像初看时那么奇怪。像新证据主义这样的理论很可能会同意您的看法。他们通常认为,如果证据真的是同等的,唯一有理由的态度就是悬置判断。然而,我的理论将焦点从“充分证据”转移到了“认知上负责的信念”。问题不在于“我支持p的证据更强吗?”,而在于“考虑到我的处境,我持有p这个信念的行为,在认知上是否无可指摘?”。
在低风险的日常情境中,我们是基于默认假设来行动的。当你看到某人进入一家咖啡店,默认的、正常的预期是他们会待上至少几分钟。相信“老王在星巴克”仅仅是基于这种正常的、实践性的假设。我的信念形成过程是无可指摘的,因为它符合事件的常规进程。另一种可能性(“他一分钟前离开了”)虽然存在,但它不是默认情况。在这个语境下,我的认知责任非常低;我不是在追踪老王的警探。我没有责任去考虑每一种逻辑可能性,只需要以一种对于当前情境而言在认知上无可指责的方式行事。
你说得对,“不需要去查”并不自动意味着“相信就是对的”。然而,我的主张更具体。当 (a) 你有支持 p 的初步证据(看见他走进去),(b) 反面的可能性 ¬p 并非默认预期,并且 (c) 由于风险低,你没有认知责任去进一步调查时,那么形成对 p 的信念在认知上是负责的(或至少,不是不负责的)。这是一个被允许的、无可指摘的认知行为。它可能不如一个有压倒性证据支持的信念那样牢靠,但如果它恰好为真且没有削弱者(defeaters),它依然可以构成知识。
2025年10月09日 03点10分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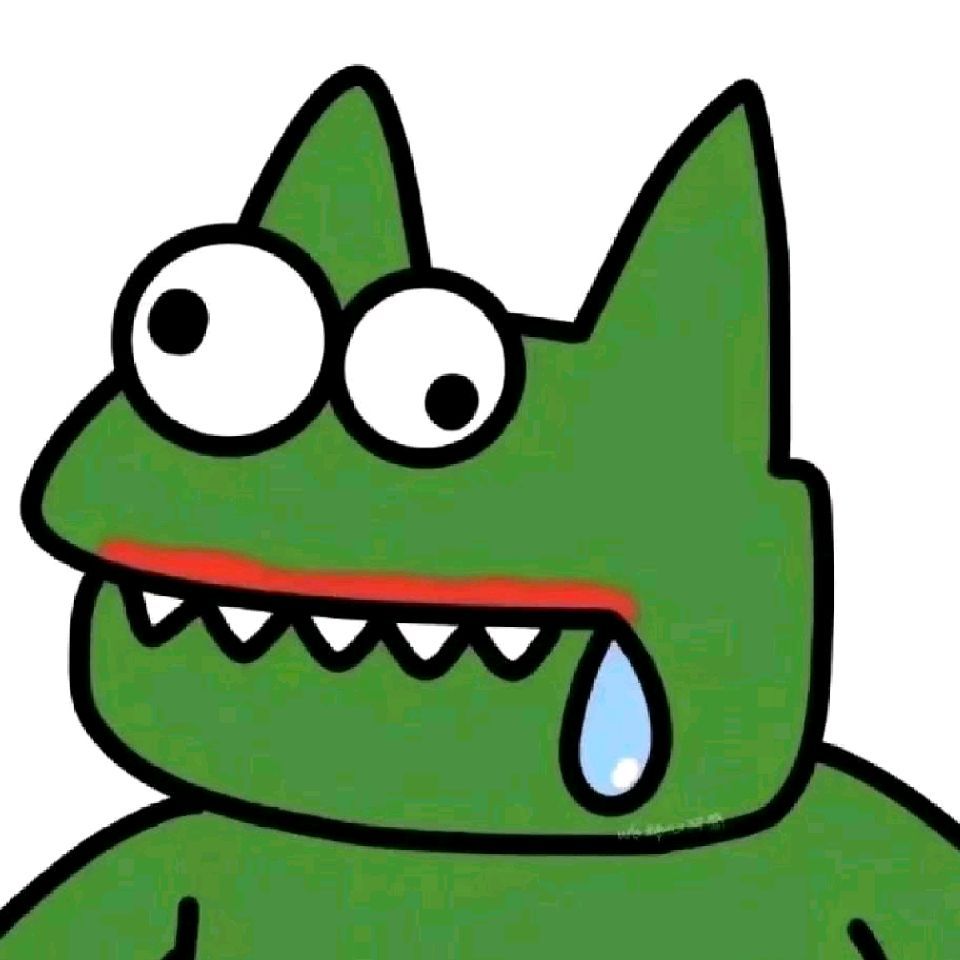
吧务
level 13
我认为胡老师对应怀疑论的许多辩点很有说服力,但仍有一处未能完全化解我的疑虑:星巴克情形与严格怀疑论情形并不相同。严格怀疑论可以被表述为——就总体证据而言,真实世界(p)与虚假世界(¬p)彼此在证据上对称。对此有人反驳说支持真实世界的证据显然更强,但我倾向于认为并非如此:长期以来被用来支持真实世界的那些证据,本质上也可以被重新解释为支持虚假世界的证据。若成立,则作者所依赖的前提——(a)存在支持 p 的初步证据——在严格怀疑论语境下并不成立。因此他的结论(即在满足 a、b、c 的条件下,相信 p 是认知上负责的)并不能直接推广到严格怀疑论的讨论;当然,在日常情境中我们确实有那种初步支持 p 的证据。
2025年10月09日 09点10分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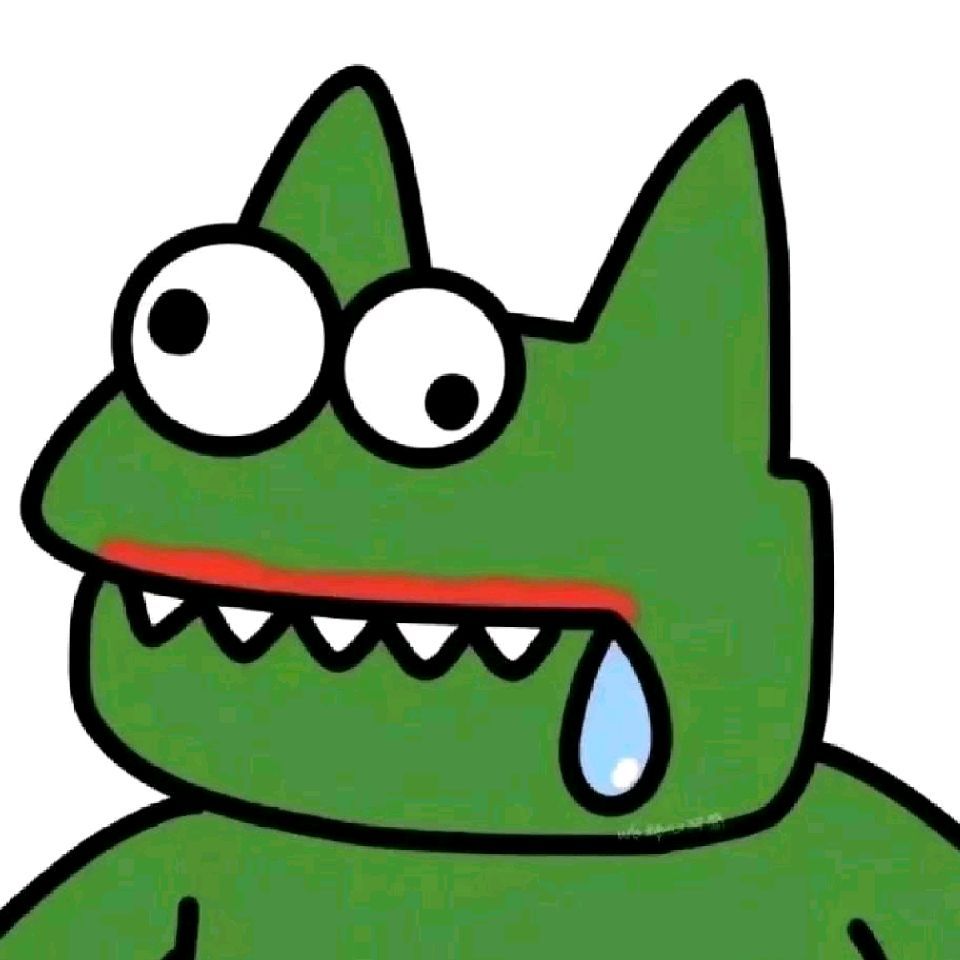
整体上我觉得对于问题1 胡老师挺好的解决了 问题2 还是有问题这里延伸下去就会追问,当然胡老师或许会说尽管 H 在逻辑或形而上学上可能,但若 H 在“现实上”不可检验、几乎不可能或没有可观测差异,就不应把它作为与 R 在证据上对等的对手
2025年10月09日 09点10分